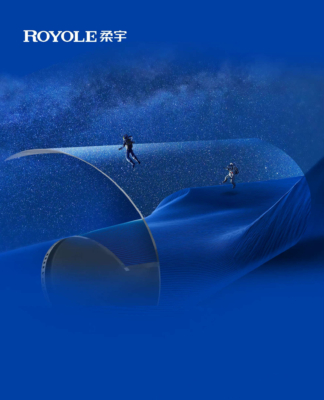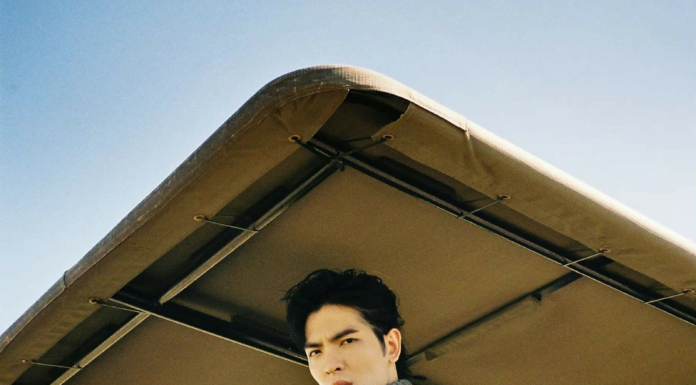免责声明:本文版权归雅昌艺术网所有,不代表CEO搜索引擎的观点和立场。
“我的爸爸是我认识的最沉着冷静的人,见到他时,谁都不会想到他是一个以爆炸为生的人。这家伙度过周末的方式就是穿着长袖内衣读报纸。”——近日,艺术家蔡国强之女蔡文悠出版个人随笔集《可不可以不艺术》,记述一个“艺二代”找寻自我的成长道路,同时也讲述女儿眼中那个炸遍全世界的“火药艺术家”作为父亲柔情的一面。

并不容易的成长之路
蔡国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蔡文悠1989年在东京出生,彼时蔡国强与妻子在日本发展得并不顺利,日子过得很艰难。“大女儿出生时候,表情里有一股勇气与自信,一个新生儿这么脆弱,对世界的种种没有任何能力驾驭,但是她的表情透露的信息,让我感到一切都会顺利。”蔡国强在他的书里说。而等到小女儿出生时,蔡国强己移居美国并且进入了事业的收获期,“小女儿出生的时候表情是幸福的。”
蔡文悠的出生以及成长,可以说与爸爸蔡国强的事业道路相伴,也是蔡国强在日本渐渐取得成功,而后转至美国,并最终获得国际性声誉的第一见证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常常没有其他同龄的孩子们的陪伴,仿佛爸爸的事业成了与我相伴的兄弟姊妹,随我到处旅行。”
蔡国强夫妇是带着孩子工作的典范,从小蔡文悠最常呆的地方就是美术馆。后来,蔡国强常常提起的一桩往事:他和太太因为工作,将还睡在婴儿床当中的蔡文悠带到美术馆,观众不知道那个睡着的宝宝是真实的还是一件艺术作品,直到发现她开始大哭。
艺术成为了童年的全部,回忆起来,蔡文悠写道“对于成长,美术馆是太过孤寂的地方”,她无所事事地待在美术馆,以免打扰正在工作的大人。为打发时间,她也帮着父亲布展,从很小开始,她就知道布置展览的每个环节,四五岁的时候她会问还在工作的蔡国强:“爸爸,你什么时候要布灯光?”因为她担心灯光没弄好,会要等很久才能吃饭。
再长大一些,她跟随父亲的展览到处旅行、勘察场地,拍摄父亲的展览现场,干着在别人看来有意义的事情,自己却常常感到无聊,有时候,她希望自己能和同龄人一样尽情的享乐青春,但有时候她又希望像父亲一样做一个优秀而重要的人。
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圈,连中国话都说得不流利的华裔女孩,头顶着父亲的光环,却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不存在。童年时,蔡文悠记忆深刻的事情是被人取笑其名字的英文发音“when you”,他们会说“文悠上厕所,文悠到这儿来……”
“于是,我变得羞于向人介绍自己,因为人们要么无法理解我的异国名字,要么立即联想起‘当你(when you)……’我失掉了勇敢的天性。有次全班同学集体出游,去见一位魔术师。我深深地迷恋魔术,很想亲身体验下它是怎么变的,然而,当魔术师邀请一位观众上台协助表演时,我竟胆怯了,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自己的名字。”
长大后,蔡文悠一直害怕与说话有关的事情,但她还是鼓足勇气去古根海姆博物馆帮蔡国强发表领奖演讲,从性格上来看,蔡文悠并不算一个外向的孩子,但是却不得不去面向人群,因为她是蔡国强的女儿,而且她是个听话的孩子,因此,父亲要求她的事,她总是努力去做到。
蔡文悠在书中非常调侃的写下一段文字,描述她从小对爸爸“无条件”信任:“爸爸说过的话,我总会很当真。在我约莫七八岁时,他习惯进餐时用温水润喉清道,嘱咐我也照做,还说不然食物便会卡在我干涩的喉咙间,使我窒息而死。我开始想象自己猝死的场面,立即从厨房打来一杯水,如实照做。从此,每逢进餐,我总会尽可能喝些流体来润滑喉咙道,免得早夭。”
“一次,爸爸随口说,人们根本不必在早晨刷牙,因为没有什么可刷的,只需用漱口水清除前晚残留的异味。虽然他不是牙医,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和知识,只是常常看些关于日常疾病的医书,掌握其中的只言片语,我却相信他。虽此,从初中到高中,我从不在早晨刷牙,尽管每年都有新的蛀牙产生。
多年后的某天,爸爸放下正在阅读的报纸健康专栏,又随口嘟囔了一句:即便我们什么都不吃,夜里口腔中依然会滋生许多细菌。之后我又立即恢复了早晨刷牙的习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习惯了这些出尔反尔的意见和零零碎碎的建议。我的信念体系和知识基础都来自过去数年中爸爸告诉我的一切。”
尽管蔡文悠对爸爸言听计从,但这个听话的孩子却并没有将对艺术的兴趣直接从艺术家父母那里遗传过来——“我对创作在美术馆或画廊中展出的作品没有兴趣。”当她开始对未来的职业产生一个梦想的时候,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那是她八岁跟父母第一次出席时装秀之后,她说:“我想设计的服装不只满足日常穿着的需要,还要有雕塑感,能表达自己的观念。我毫不介意自己设计的服装是否符合社会对于人们应穿什么的限定。我想创造这个世界上还未有过的衣装,我希望观者云集,都来看我那些轻盈自在的天才之作在高端秀场上的亮相。”
显然,蔡文悠的时装梦想具有艺术气质,只是她更希望自己做出的东西被人们使用,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不是进入美术馆。整个少年时期,她都做着时装梦,因为父亲的社交圈,蔡文悠有很多别人难以企及的机会,她热爱三宅一生,后来三宅一生常常送她礼物。
这样的幸运并不总是带来愉快,在一次酒会上,爸爸带蔡文悠认识了纽约著名的时装品牌经理人汤米.希尔费格,对方听说蔡文悠热爱时装,便邀请她去尝试做一次时装模特。蔡文悠欣然前往,却因为不能配合摄影师摆出笑容,而彻底冷落到了一旁。对方虽然不采用她的照片,却坚持付给她不菲的报酬,她开始拒收,对方却将支票再次寄过来,整个经历让蔡文悠感到屈辱。
在艺术领域,蔡国强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名人,但在这之外,情况就不一样了。“时装周后两个月,全班同学进行校外考察时经过三宅一生在SOHO区的‘三宅褶皱’专卖店。我指着橱窗中的火药龙形印花,对同学们说这是我爸爸的设计,大家全都大笑,说好丑。
有两个我还拿她们当朋友的女孩说她们也能做成那样,让小狗在衣服上拉屎,或是穿着脏鞋在面料上踩踩就成。我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却又没办法得体地回嘴,发现还是弱弱地笑笑,对她们表示赞同来得更容易,然后扭过头去,装作在看那些过往的店铺橱窗,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上大学时,蔡文悠选择进入罗德岛的服装设计学院,但还没有开学,她便感到自己与那个专业里“光鲜入时,个性斐然”的学生相比,太过相形见拙,这彻底打败了她,最终,她意识到时装梦根本不适合自己。
放弃当服装设计师这个最初的梦想时,蔡文悠写道:“我弄过一个密码锁,己经忘记了密码,我很高兴再也用不着去记它了。” 在父亲的建议下,蔡文悠申请转到了雕塑系,宿命般的走上了她从小就想逃离的艺术领域。
“我在美术馆里度过枯燥乏味的成长期,最后却选择了学习艺术,这真有些讽刺。在整个大学期间,我眼看着身边的同学,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中有许多人视艺术为生命,宁可饿着肚子挥斥激情,也不愿在赚钱更多的行业里自在安逸。而回首过去,我明白自己选择艺术学院并不是想要学习艺术或成为艺术家,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本能,想要去理解自己成长的环境。
我想理解为何罗斯科的色块使人们在画前心醉神迷站上几个小时,为何蒙娜丽莎能吸引世界各地的观者去一睹芳容。我想理解为何有些我曾觉得极度无用和刻意的东西可以被展览并卖到那么高的价钱。所以,我创作艺术,我进艺术学院去创作更多的艺术,我付出大量时间去弄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却只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想要表达什么。”
在雕塑系,蔡文悠常常感到自己并不优秀,她的作品往往不受好评,挫败感一直陪伴着她,但她很坚强,为了找到自我的人生目标,她用两年的时间整理自己的成长道路,出版了这本随笔集《可不可以不艺术》。目前,蔡文悠依旧不打算从事艺术,而是去伦敦念书,把自己定位为未来的创意人士。

艺术家式父母
身为艺术家式的父母,蔡国强夫妇对孩子的教育在某些方面称得上是百无禁忌,蔡国强喜欢去赌场,蔡文悠从小也对赌场充满向往,期待自己满二十一岁,可以进入赌场。
“自从我们搬来美国生活,去赌场就成了爸爸的正经事,每年至少做一次。他一直迷恋那里无休无止的纵乐之声,那些闹玲的轰鸣,那些梦幻般的老虎机吐钱的清脆声音,回荡在被闪烁的“777”照亮的阴暗房间。每当他进入赌场,像是踏上异国的土地,他愿意一次次地重访,乐此不疲。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赌场一样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从阿姆斯特丹到澳门,甚至朝鲜,满世界的老虎机都接纳过他投入的硬币。每当有朋友或亲戚从中国来访,爸爸都会带他们去赌场,以欢迎他们光临美国。我曾问他为何如此钏爱赌场,他对我说因为赌博在‘共产中国’是非法的,因此,我想,大概是赌场使他融入了这个新国家的文化。”
除了赌场,蔡国强和太太去荷兰的红灯区散步时,也会带上当时只有四岁的蔡文悠,“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些红灯闪烁的玻璃房子里的裸体女人。许多年后,我向爸妈说起这事,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声道歉,他们却只是被我的好记性深深折服。对于他们来说,去赌场或逛红灯区是好玩儿的‘小冒险’,我长到他们的年纪就能明白其中妙处。”
蔡文悠戏称自己是父母用来做实验用的小白鼠,被爸妈在与他们当年全然不同的文化中养大,从不知道怎样的活动适合小孩,但却也培养了蔡文悠的好奇心。
“我对新奇事物的感知是由这样两个人培养起来的,他们有着孩子般的敏感,这使他们能成为专业的艺术人士。作为成人,他们回想他们曾被迫早早结束的童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的年月,父母不在身边,他们要照顾兄弟姐妹并赚钱养家。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像做实验用的小白鼠,爸妈在与他们当年全然不同的文化中将我养大。”
正如蔡文悠在她的书中所写,从小听话的她对爸爸充满依恋,蔡国强与女儿的关系更好到一踏糊涂。从小到大,蔡文悠随时都要跟蔡国强黏在一起。只要见到面,身体有个部分就是要黏着,触碰爸爸,连吃饭的时候她的脚也要踩在爸爸的脚上头。有时候蔡国强会请她能不能不要再这个样子了。结果她回他:“这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
但从上高中之后,她就停止身体一定要跟爸爸触碰的习惯了,似乎长大了不少,也与爸爸有距离了。蔡国强身为爸爸的要求是,他希望小孩子离他有点远,可是必须在他可以看得到的距离。

我的爸爸蔡国强
虽然这并不是一本写蔡国强的书,但在女儿的生活中,爸爸蔡国强是最重要的角色,由此,从女儿笔下,也能让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蔡国强。
蔡国强一直热爱格列柯的作品。在他工作室的墙上,挂着《纽约时报》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格列柯展览做的整版广告,此外便只有他的那些火药画,全放在地上,斜倚着墙,还有一幅《X档案》“我想要相信”的海报,他暗自借用这句话作为他2008年古根海姆美术馆中期回顾展的标题。
蔡国强人缘很好,与他合作过的人常常能成为朋友,他也特别愿意将自己的成功与身边的人一起分享,女儿蔡文悠说道:“从我十几岁开始,到我二十出头,爸爸将他的每一次展览都视作他艺术成就的新高度,期待下一场展览将他带到更高的峰巅。在那段时间,他的展览遍及纽约的每个重要的美术馆和世界各地的顶级机构。”
“每当举办一场他视作里程碑性的展览,他都想要全家人一起见证和体验。他会把一大堆人运到世界各地的展场:他这边的家人,我妈妈这边的家人,娶了我家人或嫁给我家人的人们的亲戚,家人的朋友,工作室所有员工的家人,还有一些合作过的日本渔民。有这样一大帮人到他的展场去朝圣,我便也必须是这朝圣队伍的一员,如果自己的女儿没有到场,他就会觉得尴尬。”
蔡国强的创作中,他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制作他的火药画,蔡国强几乎从不亲手制作他的装置作品,他总会找来装配工人或技术专家帮他制作和安装。基于爸爸的这种创作方式,蔡文悠从小就不学写生,只喜欢创意,但是大学上了雕塑系之后,爸爸开始建议她磨练手上功夫,跟她说,不会画画,缺乏传达观念的基本技能。
在爸爸在安排下,蔡文悠还特意在北京上了一段时间的绘画培训班。“这个班要求学生们用一成不变的绘画技法每周画六天,每天画十三个小时。中国的艺术生需要长年累月地进行这种训练来通过考试进入中国的美术学院。
在美国的艺术学院学了一年却还百无一技的我报名参加了两周的培训。我忐忑地坐在一个画架前,在一个像火车站般长长的房间里,挤满了上百个踌躇满志,如饥似渴的学生,他们正对着坐在我们面前的真人模特进行一丝不苟的肖像素描。与他们精准的素描相比,我的画更像是毕加索式的肖像,却又没有毕加索那种张扬的才华。然后,经过两周的持续练习,我确实发现自己有了长足的进步。”
蔡文悠是这样认识作为艺术家的蔡国强:“我的爸爸是我认识的最沉着冷静的人。见到他时,谁都不会想他是一个以爆炸为生的人。这家伙度过周末的方式就是穿着长袖内衣读报纸。他的成功有部分是因为他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感知而不惊扰社会的秩序和安宁。我发现最有力量的总是那些能在感情上触动观者,并能被孩子们体验的作品。关于一件艺术作品语境的学院派理解并不总是欣赏作品的最佳方式。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就非常喜爱我爸爸的作品。”
回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点点滴滴,蔡文悠说:“就像那些火药创作,那些精心编排的焰火表演,那些装置作品,我也是爸爸的一件艺术作品,是他日复一日辛苦琢磨的产物,是他的性格的翻版与呼应。就像爸爸通过艺术找到了他自己,在爸爸为塑造的世界里,我也正通过探究我是谁而找到我自己。”